小程序内每天可以领取卡密
关注公众号不迷路
扫描小程序二维码领取免费卡密
可下载全站所有资源
资源类型均为百度网盘形式
请自备百度网盘账号
站内所有资源均来自网络
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
请领取过卡密的小伙伴查看卡密使用方法
第一步:点击(充值卡密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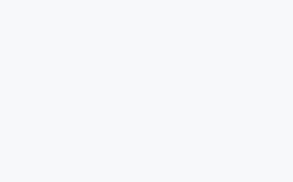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二步:选择(充值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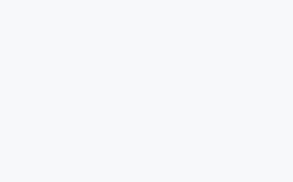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三步:选择(卡密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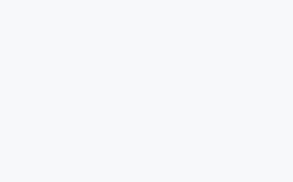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四步:输入领取的(卡密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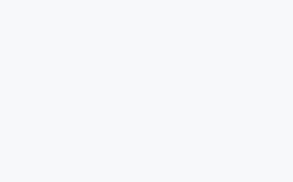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五步:点击(会员开通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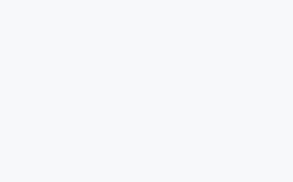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六步:点击(立刻加入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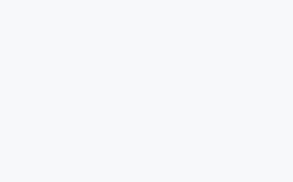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第七步:选择(余额),点击(支付)
恭喜完成会员开通,尽情下载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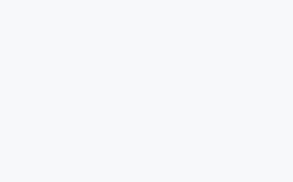
¥undefined
请打开手机使用微信扫码支付
「」
妙灵图集
× 使用邀请码,您将获得一份特殊的礼物!
请输入邀请码
打开微信扫一扫
扫码并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」安全快捷登录






